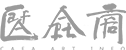在动荡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便携的卡纸、木板、自制画箱与颜料,成为赵文量与杨雨澍外出写生的全部工具。他们缩小画板、画箱,藏于书包,用随处拾取的材料亲手制作画框,这一创作习惯一直延续至新千年之后。赵文量的《神鸟》(1975)的画框便取材于杨雨澍就职的工厂的进口日本木板,保留了原始的木纹,表面蓝色由赵文量亲自上色;画面上方月牙白的圆形,与微微弯曲的绿色弧线构成日月交替的瞬间,通过两只鸽子的凝望,也许寄寓着艺术家在风云莫测的现实处境中对自由的渴望。《芍药》(1976)的画框则来自刘迅——彼时任北京市美术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的他,得知无名画会成员在文革中执着绘画,在改革开放初期突破藩篱,促成无名画会首次公开展览。他把从另一幅画上拆下的框子给了赵文量,这个框子成了其作品的一部分。杨雨澍的《桃花小碗》(1973)原本的画框是金色的,他觉得这种华丽与画作的细腻不相符,遂请师傅刷成白色。这些原始的画框,有的漆面剥落,有的表层龟裂,磨损与褶皱见证了历史真实的触感。


赵文量,神鸟,板上油画,1975年,25×33厘米
“美在斯——赵文量与杨雨澍的自由世界”,中间美术馆展览现场


赵文量,芍药,布面油画,1976年,43.5×53厘米
“美在斯——赵文量与杨雨澍的自由世界”,中间美术馆展览现场


杨雨澍,桃花小碗,三合板裱布油画,1973年,46.5×53.5厘米
“美在斯——赵文量与杨雨澍的自由世界”,中间美术馆展览现场
画箱与画框的故事,和赵文量与杨雨澍对限制的创造性转化,给予我们展览设计的灵感。“美在斯”的展览设计试图搭建物理空间与精神气质之间的通道,受到1970年代后期艺术家因地制宜自组织展览的启发,我们选择质朴的原色木板和木条作为基本语言,在展厅中搭建了一个交错的结构。我们有意地将作品全部展现在这个结构中,让墙面空出来,也可以说,这些绘画与展示它们的结构是展厅中的一个整体。
康定斯基在《艺术中的精神》(On the Spiritual in Art)(1911)写道:真正的艺术不在于再现物质世界的表象,而在于通过色彩、形态、节奏的内在力量,与观者建立精神上的共振。他对画面节奏的把握,也提示我思考如何在展览设计中唤起那种无需转译的“绘画性”和精神性。工作过程中,我用SketchUp直接进行空间实验,在强调参数化、尺度和精确性的数字系统中,回归点线面,再度探寻“绘画性”的可能性。赵文量与杨雨澍作品中纯粹的“绘画性”并非对现实事件的漠视,也很难用形式或风格概括,反而是真挚和诚实的心灵去直面生活,将美内化为生存与创作的自觉。在“红光亮、高大全”主导艺术生产的年代,他们拒绝主流宣传所塑造的统一现实,和这种不符合人体视野习惯的描摹,转而将画笔对准身边最寻常的景物——北京的街道、玉渊潭的树、家中的器物,用身边的工具作画,留白画面,和身边的朋友一起办展览,重建属于个人的美和真实。绘画性更像是一种方法,这些画作就是他们的日记,不再讲述伟大的故事,而是记录生活里具体、本真、艰辛、欢愉、苦涩和激情的瞬间。
展陈摒弃了将画作依附于墙面的惯例,让作品对称悬挂于木板两面,使其互为支撑、彼此呼应,折射二人亦师亦友的人生关系。深棕色墙面围裹着作品和文献,如同放大的画箱,重构当年微观世界的心灵图景。可拆分的木方结构既回应着艺术家日常的实践策略,也暗合赵文量画作中那些将出未出、将尽未尽的光晕、日影、天边与路途,由此延展对美的追求。



“美在斯——赵文量与杨雨澍的自由世界”,中间美术馆展览现场
自画像,赵文量,布面油画,1981年,48.5×40 厘米
青铜,赵文量,纤维板,1980年,119×91.5 厘米

刘海粟为无名画会第一次公开展览题写“美在斯”,刘海粟,1979年,
“美在斯——赵文量与杨雨澍的自由世界”,中间美术馆展览现场“美在斯”展聚焦赵文量与杨雨澍1970年至1982年间的创作。以走廊中两位艺术家的肖像为序曲,让展览叙事通过个体目光展开,回应艺术史中肖像见证历史的传统,也在经历标准形象主导的集体面孔之后,重新以个体目光把握主体性,确立视线的尺度。赵文量的《自画像》(1981),闭目沉思、胡须微扬,笔触粗粝却不失温柔与平和。在私人空间被公共叙事摧毁之后,映射出自我修复的力量与内心领地的坚守。赵文量为杨雨澍画的肖像《青铜》(1980),以稳健的笔触捕捉了其神态,坚毅而安定。入口右侧悬挂刘海粟于1979年为第一届无名画会展览题写的“美在斯”——美存在于人的情操、艺术、社会生活与大自然,作为展览标题和精神起点。展台上同年出版的卞之林诗集《雕虫纪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则与当时改革开放初期的“美学热”形成互文。这本出版及售罄的诗集,与赵文量、杨雨澍的作品有着相契的冷静抒情,也共同见证了个体表达在文艺领域的艰难复苏。

“美在斯——赵文量与杨雨澍的自由世界”,中间美术馆展览现场(上杨雨澍,下赵文量)赵文量与杨雨澍自熙化美术学校相识以来,始终保持着亦师亦友的生命情谊。和无名画会中的其他成员一样,他们并非职业的艺术家,白天工作,没有专属的画室,夜晚与周末才能作画。二人保持完整的个体脉络,同时在生活与精神上互为依托,差异与连接并存。这种关系也成为展览架构的基础,力求达到既敞开、透气,又聚合、并行。展厅中的双面木板按从左至右,从外至内的序列编排绘画,分别呈现两位艺术家各自的创作,对应两位艺术家的独特的气质。面朝入口的外侧木板陈列杨雨澍的绘画——活泼、明快,色彩轻盈而富有青春气息,如迎面而来的召唤。刘海粟评价他:“杨雨澍的画笔简意繁,本质是一位感情细腻的诗人。作品在现实中扎根既深,又常常笼罩着一层浪漫主义情调。他画的海更接近德彪西的同名交响乐。”背对入口的内侧呈现赵文量的绘画——内敛、忧郁,心思细腻,蕴藏强烈而深沉的象征意味。刘海粟评价他:“赵文量是一位基本功扎实,技法老练、变化很多、感觉敏锐的画家;又是一位律己甚严、诲人不倦、不计酬劳、颇能因材施教,善于帮助后劲发展自己艺术个性的良师。”每一列木板单元以主题分组呈现了两位艺术家的实践,这些写生多源于北京及其周边的日常景观,涵盖静物、风景、鸽子和人群等,在都市边缘捕捉动荡年代中自然与人性的交织。
 “美在斯——赵文量与杨雨澍的自由世界”,中间美术馆展览现场
“美在斯——赵文量与杨雨澍的自由世界”,中间美术馆展览现场
展厅左侧的一组静物和写生,杨雨澍采用大色块和明显甚至突兀的笔触,勾画出物与自然的涌动。从右侧开始,1972年的《动物园树》《五色土》到1975年的《瑶池》《高调子》,画面由沉稳的青绿和褐土转向明快的天蓝。继而呈现的作品聚焦他钟情的公园、静物与人物,冷峻色调中透出平面化的装饰意趣。在随后一组作品中,树木与桥的反复出现,尤以斜靠在树旁微微眺望的视角,凸显其与自然形式的亲近。
展厅左侧,赵文量这组绘于“文革”后的作品以静物承载隐喻。展厅右侧的开端是一组高度精神性和象征性的作品。《偷听音乐——致爱丽丝》(1975)描绘了杨雨澍和赵文量的女儿赵秀在朋友家中偷听西方音乐的场景,逆光之下,人物化为剪影。窗边洒落月亮的光明,悄然却暗涌波澜,潜藏着幽微却持久的指引力量。随后一组作品聚焦不同时刻的天气变换——清晨、雾气、风雨、夜色等。《红天》(1975)以单纯醒目的红色营造强烈对比,帅意挥洒,《羽毛太阳》(1974)则绵软雾化。


 “美在斯——赵文量与杨雨澍的自由世界”,中间美术馆展览现场我们也用亚克力板装裱的方式展出部分没有框子的小幅画作。一方面,从物理属性考量,这些作品通常尺幅较小,部分画在包装纸上。亚克力作为一种轻便的材料,在某种程度上与艺术家当时的创作条件不谋而合,极简的造型则避免让装裱语言在视觉上压倒画作本身。另一方面,在展览叙事层面,我们有意地将主题相近的画作聚合同框,通过这样的拼贴与组合,探索作品间的内在关联,让每一块亚克力板和其中的画作成为一个独立的章节,在展览中再构建一个展览。例如赵文量的《上坟》(1979)系列作品,描绘了大姐、二姐、春森上坟的场景,和父亲的墓冢,直面私密的记忆。画面使用大块的笔触,一幅似为另一幅的草稿,相似的母题中反复出现泥土的棕褐与植被的暗绿,点缀人物服装的亮色打破沉闷,暗示生者的情感波澜,快速扫过的痕迹如灵动奔放的叹息。还有一片亚克力板汇集了赵文量对于天气和季节的描绘,从日月到心灵。
“美在斯——赵文量与杨雨澍的自由世界”,中间美术馆展览现场我们也用亚克力板装裱的方式展出部分没有框子的小幅画作。一方面,从物理属性考量,这些作品通常尺幅较小,部分画在包装纸上。亚克力作为一种轻便的材料,在某种程度上与艺术家当时的创作条件不谋而合,极简的造型则避免让装裱语言在视觉上压倒画作本身。另一方面,在展览叙事层面,我们有意地将主题相近的画作聚合同框,通过这样的拼贴与组合,探索作品间的内在关联,让每一块亚克力板和其中的画作成为一个独立的章节,在展览中再构建一个展览。例如赵文量的《上坟》(1979)系列作品,描绘了大姐、二姐、春森上坟的场景,和父亲的墓冢,直面私密的记忆。画面使用大块的笔触,一幅似为另一幅的草稿,相似的母题中反复出现泥土的棕褐与植被的暗绿,点缀人物服装的亮色打破沉闷,暗示生者的情感波澜,快速扫过的痕迹如灵动奔放的叹息。还有一片亚克力板汇集了赵文量对于天气和季节的描绘,从日月到心灵。
“美在斯——赵文量与杨雨澍的自由世界”,中间美术馆展览现场
文/李慧一
图文资料由主办方提供